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大街100號(北樓)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一層 Email:info@landscape.cn
Copyright ? 2013-2022 景觀中國(www.36byz.com)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68035號
 京公海網安備 110108000058號
京公海網安備 110108000058號
7 月 4 日晚上,大連《半島晨報》上的一則政府通告讓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孫康感到震驚。
通告宣布:為了防治森林病蟲害,7 月和 8 月的每月 7~15 日,市城建局將對中山、西崗、沙河口三個區,以及大連市風景園林處、大連市森林動物園和大連市老虎灘海洋公園進行“飛機撒藥”,噴一種叫做“噻蟲啉”的殺蟲劑。通告要求市民關好門窗,不要在外晾曬衣物,減少林間戶外活動,并說“飛防用藥對人畜禽無害”,但承認“對家蠶、蜜蜂等昆蟲有一定影響”,因此要求“作業區內從事養殖的單位和個人做好相關防護工作”。
孫康對這種農藥聞所未聞,通過查詢資料得知這是一種“新煙堿類”農藥,對昆蟲、鳥類都構成威脅。歐盟因此已經禁止了其中三種的戶外使用。
第二天下午,孫康和一位記者、一位野生動物保護志愿者一同來到市城建局,就此事進行溝通。工作人員告訴她:大連在 2016 年發生松材線蟲疫情,2017 年曾兩次用飛機噴藥,噴的同樣是噻蟲啉,但是今年發現疫情仍然存在,所以要繼續噴。中山、西崗和沙河口都是大連人口稠密的核心區,而在發布通告之前,政府并未對噴藥進行環境評估,也沒有公開征詢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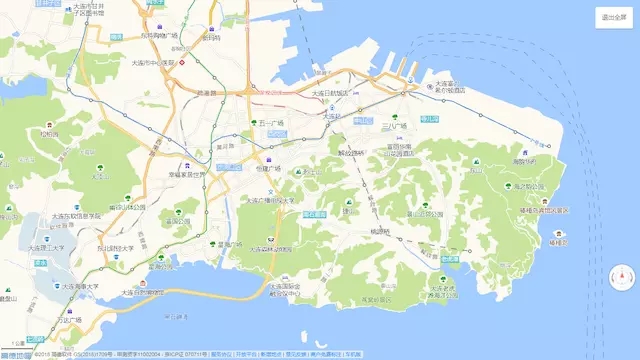
7月7日大連上空的撒藥飛機 圖片由孫康提供
溝通沒能阻止噴藥計劃。7 月 7 日上午,孫康在位于沙河口區的家里看著一架輕型直升機從上空掠過,憂心忡忡。
在中國,農業中的農藥使用被高度關注,但是城市綠地中的農藥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盡管“飛機撒藥”并不常見,但有研究顯示,“常規”的使用也不那么令人放心。
2013年,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盧曉霞來到哈佛大學訪學,研究的就是新煙堿類農藥(neonicotinoids)。一年后,她回到北京,著手研究這類農藥在北京和天津城市環境中的殘留情況。今年 2 月,其中關于天津的研究論文率先發表在國際期刊《分析化學學報》(Analytica Chimica Acta)上研究發現:在天津的 35 座公園和 33 座住宅區的土壤中,新煙堿類農藥殘留濃度并不低于已知的農田水平,公園中的殘留水平尤其高,能達到經常使用農藥的大棚里的水平。
盧曉霞告訴記者,對北京的研究尚未發表,但是數據呈現出和天津相似的情況。另外,對兩座城市的研究還只是測量殘留量,還未評估其環境和健康影響,但是現有的研究表明:新煙堿類農藥對包括蜜蜂在內的眾多無脊椎動物都會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會造成一種叫“蜂群崩潰紊亂”的現象,使蜜蜂數量在北美和歐洲大幅下降,以至于讓人們擔心影響植物的自然授粉。它也會影響脊椎動物。例如,如果鳥類吃了被它毒死的蟲子或用它包衣的種子也會受到毒害。新煙堿類農藥對大鼠腦神經元煙堿乙酰膽堿受體有興奮效應,因此可能對人體健康也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會危害發育中的大腦。
城市人口密集,人們有大量機會與綠地植物近距離接觸,比如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卻對哪里噴過農藥、噴的是什么、噴了多少一無所知,而且往往不存戒備。
“公共綠化農藥的確是個問題。”上海市農委種植辦的李姓負責人在電話中說。但這不歸農業部門管,他說:“農委只負責管理農業的生產和銷售,綠化操作領域,是綠化市容部門的事情,綠化市容部門有責任在自己的工作中落實《農藥管理條例》。”去年頒布的新《農藥管理條例》中規定:除了農業主管部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負責有關的農藥監督管理工作。”
上海市綠化管理指導站是上海市綠化和市容局下屬的一個對防治綠化病蟲害進行技術指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的機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其實上海綠化部門從 20 年前就開始提公共綠化的“無公害養護”,他所在的機構也一直向全行業提倡“生態養護”、“綠色防控”,比如用生態藥劑替代化學藥劑,用粉劑、水劑替代滲透性更強的乳油劑扽等,此外政府在綠化養護招標中,也會要求競標企業使用生態養護原則,毒死蜱、辛硫磷等藥物是不鼓勵企業使用的。
但他也承認,上述這些都不具有強制性。農業主管部門有專門的行政執法部門來管理農藥使用,但綠化市容部門沒有。因此,實踐中還是有養護單位在用像毒死蜱之類比新煙堿類更毒的有機磷農藥。關于毒死蜱,他補充道,這種藥價格便宜,效果立竿見影,往樹上一噴,蟲子刷刷往下掉,省時省力。在需要應付上級臨時檢查的時候,就尤其管用。


2017 年 8 月,上海街頭的綠地農藥噴灑裝置 攝影:蔣亦凡/好奇心日報
據他觀察,養護單位之所以依賴化學農藥,很大程度上是壓縮成本的需要。近幾年上海的綠化養護實行“屬地化管理”,把養護責任下放到區和街道基層政府,結果,政府招標預算定額被定得很低。于是,對承包企業來說,又經濟又高效的化學農藥,就成了縮減成本的首選。相比之下,生態農藥要比化學農藥貴好幾倍,效果還不那么明顯,平添人工成本。此外,養護工人的薪酬水平過低,有不少還是領取日薪的臨時工,讓操作的規范性更加難以保證。
但這也不全是養護的問題。綠地之所以要噴藥,根子往往是在建設中埋下的。“建設中有非常多的問題,比如規劃不合理、病蟲害人為傳帶、引入不適宜的品種,等等。養護經常是在給建設擦屁股”,他說。
一位景觀設計行業的專業人士表明,建設方不愛鄉土品種,有經濟誘因存在,因為外來植物比較貴。今年 2 月,《新京報》的一篇評論在批評城市綠化“南樹北種”之類的奢靡風的同時,提出要公開城市綠化建設的預決算。
黃越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的博士后,她說自己最大的興趣是在城市綠化中推廣生態方法。她從本科到博士,學的都是風景園林,做過景觀工程的規劃設計。她說,中國一塊城市綠地的誕生,先要經過規劃、設計和施工,在施工完成后,施工單位通常養護一年,然后將其交給養護單位管理。但養護單位是沒有機會介入前三個階段的工作的。而規劃、設計者所追求的價值,基本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整潔”和“美觀”。比如,每個季節都有花可看、常綠樹要達到多少比例、植物有沒有病蟲害等等。為了植物健康美觀,就要定期噴藥。雖然技術規程原則上都會要求使用低毒藥劑、生物藥劑,但現實中卻沒有評估。
黃越說,“比如北京春天飛絮嚴重,就是因為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種了太多以楊柳科植物為代表的速生樹種。而槐樹種得太密的地方,就容易滋生槐尺蠖(一種以槐樹葉為食的蛾類)”,她認為如果前期建設更合理,現在也就不必給楊柳打針、給槐樹打藥了。
崔新婷是首都經貿大學會計系的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是環境審計。原本不關心綠化的她在 2015 年偶遇北京一所大學全校更換草皮,繼而發現北京高校乃至公共綠地普遍經常更換草皮,才意識到北京原來有那么多草不是自己長的,于是開始研究綠化問題。這些看起來整齊、美觀、板寸般的所謂“冷季型”草皮,都是外來品種。它們不耐旱,需要大量的水來澆灌,也不固土保墑,與住建部提出的“海綿城市”理念背道而馳。而且由于缺少生物多樣性,這樣的草坪容易滋生病蟲害,讓打藥在所難免。由于缺少昆蟲和微生物維持土壤健康,草坪下的土壤也變得貧瘠、板結,于是化肥和營養液也就成了標配。這些嬌貴的草皮,長則三五年,短則幾個月就得更換一次,不然就變成公共荒地。
崔新婷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就應該用適應能力更強的本地鄉土雜草來取代人工草皮。她把這濃縮成一句口號——“讓雜草長”。北京昌平的金榜園小區就是一個“讓雜草長”的實驗。金榜園 2001 年建成時種的是每平米 200 元的法國“草地早熟禾”,到 2008 年全部退化。物業公司表示,物業費未漲,但更換和養護草皮的成本都太高,因此拒絕更換。2015 年,居委會、居民和物業公司開始合作,有計劃地播種、培植耐旱、美觀的本土野花野草。他們發現,這樣混合生長的植物群落,更耐旱,更欣欣向榮,春天開花更早,全年花期更長,蟲害少,無需打藥,而且也不會失控瘋長。
無獨有偶,近年來屢屢發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綠發會”)在 2016 年也提出了個“讓野草長”的倡議,希望以此保護植物基因資源,保護昆蟲,改善城市水系,同時反對“南樹北種”的綠化亂象。
挪威首都奧斯陸也在“讓野草長”。據英國《衛報》去年的報道,奧斯陸從 2016 年起已經在市區開辟了十幾塊具有本地野花野草和生物多樣性的都市草甸(meadows),同時鼓勵居民把自家庭院草皮也改造成草甸,希望它們能成為城市的“昆蟲走廊”,恢復蜜蜂和其他昆蟲數量,以此來扭轉該市生物多樣性隨人口快速增加而下降的趨勢。據說保護生物多樣性已經成為奧斯陸市政規劃的核心命題。
黃越最先是在北大校園里實踐自己對“生態綠化”的濃厚興趣。2016 年,她代表自己學院的“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校園林科商量,是否能在鳥類和植物豐富度比較高的區域采取尊重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方式,比如不噴灑農藥,不清理枯枝落葉,讓有機質回歸土地的同時,創造動植物生境。他們把這些意見寫成了一份《北京大學生物多樣性管理計劃》交給校方。
2017 年,黃越的合作導師、北大生命科學院教授呂植提醒她,不如用“自然保護小區”來做這個保護。“自然保護小區”是一種小型建制,旨在保護面積小、不夠自然保護區標準卻又值得保護的區域, 1992 年在江西婺源出現了第一個,1995 年婺源的經驗得到國家林業局的推廣,截至去年全國已有 4.84 萬個。它們通常始于民間自發的保護意愿,而且保護形式靈活。
于是黃越和同事向學校提議:在校內 42.5 公頃的范圍內設立“北大燕園自然保護小區”。目前北大已經為此提議舉行了多次論證會,結果還有待批復。黃越覺得如果能批下來,北大校園就有可能成為更多高校、公園的榜樣。


北大生科院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成員在為“北大燕園自然保護小區”做生物監測 圖片提供:黃越
黃越在做的另一項工作,則有望從制度上改變各類綠化建設、養護實踐。
從去年起,她和同事受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委托,開始參與起草《城市綠地鳥類多樣性及棲息地質量評價技術規程》,并將于今年年底完成,目前正在網上公開征求意見。在這之后,她還會繼續參與另外一到兩份關于綠地生物多樣性恢復和管理技術規程的起草。這將是國內最早用“生物多樣性”來指導城市綠地建設和養護的嘗試。黃越希望它們能被賦予一定的約束力,比如成為政府招標的要求。在德國,國家層面的《聯邦自然保護法》和州層面的《柏林自然保護與景觀管理法》都明確要求城市綠化要保護生物多樣性,中國的大城市也是時候考慮這些了。
劉悅來是同濟大學景觀學系的教師。2017年 6 月,他在“一席”的演講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他在其中反思了主流景觀設計花費高昂、破壞環境,而且不為市民真正擁有和使用。他向聽眾介紹了自己反思多年的成果,那是 2014 年以來他的非營利機構“四葉草堂”在上海楊浦開展的兩個項目——“火車菜園”和“創智農園”。
火車菜園地處淞滬鐵路支線的一側,占地 7 畝;創智農園則是夾在五角場新舊兩個小區之間的一條狹長地塊,占地 3 畝。兩者都曾是長年堆積建筑垃圾的公共地塊。四葉草堂獲得政府或開發商委托后,先把垃圾清空,再在露出的土地上堆積枯枝敗葉等有機質,讓土壤恢復活力,然后慢慢種上多樣化的植物——蠶豆、油菜、藍莓、桑葚和香草……他們給火車菜園挖了條水渠,給創智農園建立了雨水收集和灌溉系統,慢慢地,青蛙、蜻蜓、龍蝦、白頭鵯、烏鶇等相繼出現。
人也聚了起來。越來越多的居民來這里看看植物、干干“農活”,或者來到集裝箱改成的社區中心里聽個關于社區營造或有機農業的講座,有時農園還用自己小小的收成,搞一個“食物派對”。公共綠地就這樣不再是“綠色禁區”,而是豐富社區生活的公共空間。

2017 年 9 月,孩子們在創智農園幫忙打理水塘 攝影:劉悅來

2017 年 9 月,在創智農園玩耍的孩子 攝影:蔣亦凡/好奇心日報
在這兩個項目成熟之后,借上海這兩年推動“城市微更新”,四葉草堂進入 30 多個居民小區和學校,選取其中植被狀況較差的區域,開辟出面積在 200 平米左右的微型“社區花園”。他們培訓居民和學生,把這些角落變成全年生長百十來種植物的“百草園”。
劉悅來最近也參與起草了個標準,這就是四葉草堂與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共同發起的《社區花園生境認證系統》。劉悅來說,在這個系統中,農藥是完全禁止的。除此之外,它鼓勵枯枝落葉回歸土地、使用鄉土品種植物、多使用植物的自播種而非外購商品種子。它還鼓勵社區居民身體力行參與到農園的勞動和管理中去,比如在家制作廚余堆肥用于肥沃土地,盡量減少外來投入品的使用。
但是市民的共識,將最終決定這些價值能否被落實到城市綠化實踐中。崔新婷說,金榜園也有看不慣鄉土草種的,叫罵著要割雜草、噴除草劑。黃越在工作中也了解到:綠化管理部門確實有生態養護的意愿,有時無奈噴藥,僅僅是因為對蟲子容忍度低的居民的舉報。
劉悅來希望,他的認證系統可以成為住宅小區、公園、社區花園、居民、景觀設計師等各方在共識基礎上主動采納的一個標準,但“如果政府愿意拿來用,那也很好”。只不過 ,他認為“如果生物多樣性沒有成為居民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任何變化都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在這個認證體系中,社區營造和生物多樣性一樣重要。
7 月 8 日大連下雨,孫康估計飛機沒來噴藥。不過她管不了這么多,在外面忙活了一下午。她在中午接到大連森林動物園打來的電話,說有市民在路上撿到一只受傷的紅角鸮雛鳥送來動物園,請她過去幫忙救治。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大連市旅順口區野生鳥類保護協會發起人,從事野生鳥類保護已經 10 年,曾經與政府合作,成功把“千年鳥道”老鐵山上的鳥網控制住,同時成為受困鳥類救護的專家。大連是世界八大鳥類遷徙通道之一,有野生鳥類 300 多種。時值初夏,正是大量雛鳥開始學飛的時候,所以經常會有失足的小鳥需要救助。她答應動物園把紅角鸮接回家,養好了就把它放歸山林。接到紅角鸮回家的路上,她再次接到動物園的電話,告訴她有人在連勝街路中間又發現了兩只喜鵲的雛鳥,她和學生趕去找到那兩只雛鳥,把它們放回樹上,親鳥很快找到了它們。
去動物園之前,她給園方寫了一份建議書,把飛機噴藥的事情做了個說明,指出動物園本身也位于本次噴灑范圍之內,建議雙方開展合作,弄清實際的噴灑覆蓋范圍,并觀測哺乳動物和鳥類所受到的影響。
孫康說自己以前從來沒有關注過農藥對城市環境的影響,但現在這是一個開始。她想做些“實實在在的研究”,弄明白飛機噴灑農藥對環境、動物和人究竟會造成什么影響。
“既然已經噴了,那就要把握住研究的機會”,她說。
本文轉載自好奇心日報,點此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