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大街100號(北樓)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一層 Email:info@landscape.cn
Copyright ? 2013-2022 景觀中國(www.36byz.com)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68035號
 京公海網安備 110108000058號
京公海網安備 110108000058號
5 月份,在探討中國環境問題的 NGO “中外對話”的網站上,發生了一場中國是否正面臨一場“水危機”的辯論,讓一個曾多次引起矚目的議題,再次浮現在眾人眼前。
引發這場討論的是 Charlie Parton (彭朝思),他是英國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RUSI)——一個創立于 1831 年的英國防務和安全智庫——的研究員(associate fellow)、英國下議院中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特別顧問,在 37 年的外交生涯中,有 22 年在陸港臺三地工作。在 2016 年退休前,曾擔任歐盟駐華代表團參贊。5 月 9 日,他在中外對話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能戰勝迫在眉睫的水危機嗎?》的報告,在其中闡述了中國正在面臨一場“水危機”的理由。兩天后,中外對話發表了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地理學者 Sarah Rogers 與 3 位同事合作的反駁文章《重新審視所謂“中國水危機”》。5 月 25 日,Parton 再次發表了自己對反駁的反駁。
“中國北方缺水”是如何被定義的
談論中國面臨一場“水危機”,Parton 的理由來自數字,而這場危機,首先出現在北方:
中國人均水資源量已經很低,低于國際公認的“緊張”線 1700 立方米,2016 年僅為 1028 立方米。但是,中國 80%的水資源都分布在南方,因而北方的人均水平其實還要更低。4 個總體上屬于“北方”的省,甘肅、 陜西、遼寧和江蘇,人均水資源量介于 500~1000 立方米之間,屬于“短缺”。 而天津、寧夏、北京、山東、上海、 河北、河南和山西這 8 個省份則更是低于 500 立方米,屬于“嚴重短缺”。 其中,京津冀地區的水平其實只有“嚴重短缺”標準的一半,“比沙特阿拉伯也好不了多少”,報告中寫道。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報告同時指出,上述 12 個水資源短缺和嚴重短缺的省份,不僅有著全國 41% 的人口,而且貢獻了農業總產量的 38%,發電總量的 50%,以及工業總產量的 46%,這些產業都大量耗水。此外,85% 的煤炭位于這些缺水省份,煤礦也是耗水大戶。這意味著,缺水將給中國的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Parton 認為,缺水不是暫時性的氣候問題,不是來自“干旱”,而是因為資源基礎被破壞了。
報告提及,2015 年中國北方三大河流——海河、黃河和遼河的水資源開發率(用水量占水資源可利用量的比率)分別高達 106%、83% 和 76%,遠遠超過了世界公認的安全警戒線 40%,以至于,比如黃河的徑流量只有上世紀 40 年代的 10%,大部分支流長期處于斷流狀態。據 2015 年一位環保部官員的說法,過去 20 年中國共有 2.8 萬條河流消失。地表水的短缺,使得北方地區嚴重依賴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以每年 1 到 3 米的速度快速下降。北京自上世紀 70 年代起,地下水位已經下降了 100~300 米。而且可能終究都無法回升,因為地下水位下降會造成含水層坍塌,不可逆轉。由此,未來城市的蓄水能力也變得更差了。
污染似乎也是積重難返。2015 年,監測水域中有 8.3% 屬于劣 V 類水質。另一個數據是,2014 年,中國有 61.5% 的地下水屬于 IV 類和 V 類污染。這些數據尤其值得注意是因為:這些由于過分污染而無法使用的水,也被算在原本就已十分緊張的“水資源”中。
讓困境成為 Parton 所說的“危機”的,是所有補救措施似乎都無濟于事。比如在說到淡水資源短缺時,人們常會想提起的海水淡化,其實有著巨大的能源局限。因為無論是反滲透和蒸餾技術都需要電,把淡水從海邊輸送到內陸也需要電。報告中寫道:“將 1 立方米海水淡化并從沿海輸送到內陸,其所需的電力生產過程就需要消耗 0.5 立方米水。”
更糟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南水北調工程可能也于事無補。報告提到:即便南水北調工程 2030 年東線和中線成功實現設計輸水量 209 億立方米,并且這些水被全部送往京津冀地區,那么也只能使這個地區的人均水資源達到人均 500 立方米“嚴重短缺線”的 2/3 的水平。可事實上,京津冀還要和山東、江蘇與河南分享這些水。因此,Parton 認為,“這項工程也只是延遲危機發作的時間而已。”
在這種局面下,Parton 認為,如果出現嚴重干旱,就會讓中國的水資源提前耗盡。這會導致經濟的崩潰。
引發的爭論:這是人口問題,還是污染問題?
相比于 Parton 的旁征博引, Rogers 團隊的反駁文章看起來有點潦草。這篇兩千字的文章的基礎是 Rogers 與另外 8 名同事一起開展的研究計劃——“中國南水北調工程的技術政治”。他們從這項研究中所獲的發現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沒有受到水資源供應短缺的威脅,且在不久的將來也不太可能受到威脅。”
Rogers 團隊對 Parton 報告的核心批駁,是他所賴以衡量中國水資源短缺情況的參照系統有問題——1700、1000 和 500 立方米的緊張、短缺和嚴重短缺三級劃分,是法爾肯馬克水壓力指數(Falkenmark Water Stress Indicator)的水壓力標準。但是 Rogers 團隊認為,Parton 不加批判地套用了這個非常簡化的衡量標準。因為,首先這個代表人均淡水占有量的指標沒有考慮人對水的需求量。Rogers 團隊認為中國人對水的需求顯著小于發達國家城市居民,因為他們住在樓房里,不澆園子,還有很多農民不用抽水馬桶。據一項研究顯示,北京居民的年均用水量比墨爾本少 50% 到 75%。此外,法爾肯馬克指數也不考慮廢水循環利用的情形,而北京恰恰在這方面做得很好——1/4 的水都是再循環水,以至于地下水位都已經開始回升。
因此,“這場危機可能被夸大了”,文章寫道,“總體來說,華北需要的不是更多水,而是更好地管理其所擁有的水資源,這包括加強污染防治和提高用水效率。有跡象表明,這兩方面都有所進展。”
他們認為,2016 年啟動的“合同節水管理”和“中國水權交易所”表明中國政府正開始為提高用水效率提供激勵機制。此外,“三條紅線”(指 2012 年的《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水十條”( 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河長制的出臺,以及 2014 年國務院 2 萬億治污撥款的宣布,以及 2018 年的行政機構改革,都讓人“有理由對中國解決水污染問題持樂觀態度”。
作為一個研究南水北調的團隊,他們認為,南水北調和在建的上百個連通不同水系的小型水利設施,配合水權交易,正讓一張能夠靈活調水的“國家供水網”鋪展開來。有了它,“水供應將不會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

2013 年 12 月,南水北調中線干線河北段工程全線貫通時新華社制作的圖表,包括工程線路示意圖 來源:中國政府網
為了進一步加強說服力,文章還從政府的行為倒推水資源的現實狀況。它說,如果缺水,北京就不會每年使用超過 10 億立方米澆灌公園綠地,中央政府也不會敢于宣布建設雄安新區。雄安獲得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支持,并從黃河引水補充白洋淀。
但是 Parton 并沒有被說服。在 5 月 29 日發表的“對反駁的反駁”中,他承認法爾肯馬克指數確實有其局限性,但即便將需求差異納入考量,華北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也還是低于發達國家太多——京津冀地區人口是英法意三國的兩倍,但是水資源卻只有英國的 10%。他同時批評 Rogers 團隊的文章過分強調飲用水(potable water),但是飲用水僅占所有水資源中的 14%,因此即便中國人用水比發達國家居民更少,也不會省出太多來。真正的用水大戶農業、工業和發電,才是問題的關鍵。
雖然 Parton 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污染給水資源造成的減損,但是他并不同意 Rogers 團隊反駁文章中“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廣泛的水污染造成的”的說法,因為根據中國官方數據,只有 8.3% 監測水域是因為過分污染而無法使用。因此即便治理成功,也不會增加太多的水資源。但他并沒有提“2014 年中國 61.5% 的地下水屬于 IV 類和 V 類污染”的問題,這看起來可是很多水。一種解釋可能是,地下水污染非常難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因此無需討論。
與 Rogers 團隊的說法相左,他所引用的來自北京市水務局的說法,只不過是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已經減緩,而水位回升還要等到 2025 年。對于 Rogers 對北京和雄安的強調,Parton 認為,北京和雄安因為其特殊地位,都不能代表華北。
遠水是否解得了近渴?
雙方最核心的分歧,還是圍繞著南水北調工程和一張“全國水網”解決中國缺水狀況的潛力。
Parton 認為,在地形復雜、幅員遼闊的中國談論全國水網,過分“愚公移山”。戲劇性的是,他還找出了 Rogers 在 2015 年與上述“中國南水北調工程的技術政治”團隊中的 4 名成員聯合發表的一篇論文,其中寫道:“由南水北調工程現有路線所轉移的水量必須減小,工程的進一步擴展計劃必須擱置。隨著其局限性變得清晰,南水北調工程很可能成為中國用大工程解決水問題的最大的失敗。”《好奇心日報》看到論文摘要中還寫著:“更好的本地水管理,而不是橫跨國境的抽水,才是滿足不斷增加的用水需求的正確方式。”
為什么 30 個月前的質疑,到現在就樂觀了?Parton 提出了新的問題。
實際上,對南水北調的爭議一直存在,質疑的聲音甚至來自政府高層。
2014 年,原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博士發表在《給水排水》期刊上的論文《我國城市水安全現狀與對策》指出,諸如引黃濟青、引漢濟渭、南水北調等“外調水”的模式已陷入困境,造成調出地生態破壞,而且調來水與流入地水因為成分差異,出現自來水管道內水垢析出的問題,相當難以治理。治理水污染、恢復水生態、提高用水效率才是保障水安全的正確思路。
2015 年,一項中美英四所大學的聯合研究,據說是首次全面分析了中國 2007 年以前的以水利工程形式實現的“物理調水”,和以耗水產品的貿易實現的“虛擬調水”,發現無論是“物理”還是“虛擬”,都沒有在緩解受水地水壓力中扮演主要角色,卻加重了輸出地的水壓力。而關于未來,該研究測算發現,到 2030 年,南水北調輸出地湖北的水壓力指數將從“中等”轉為“嚴重”,而另一個輸出地江蘇原本就處于“極端”水平的水壓力,將進一步加重。“極端水壓力”的含義是,該省年度用水量已經大于其年度淡水更新量,因而水資源存量將不斷降低。研究團隊的結論是,為了緩解水壓力,中國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加強用水需求管理,提升用水效率,而不是繼續改變水的供給。

一段尚未通水的南水北調水渠 來自 flickr 用戶 evic dong
2009 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水文水資源學家、中國科學院水問題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劉昌明在接受《科學時報》采訪時,對南水北調也有個樂觀的預期。他說:“盡管目前北京市每年仍然靠超采 3~4 億立方米的地下水來穩定水需求,到 2014 年南水北調中線的水到來以后這一問題將會解決。”
但 2014 年的時候,情況還是出現了變化。他在這年再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 2011 年對漢江水源區水量情況的調查,2000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間水量減少了 71.8 億立方米,讓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原先設計的 95 億調水量,“可能會出現一些緊張的情況”。
除了調水還能做什么?
劉昌明院士在 2009 年回答記者“我國水資源未來能否支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需求?”的問題時,他表示自己很樂觀。
樂觀的一個理由,與他對什么是“水資源”的理解有關。通常對水資源的理解是地表水與地下水之和,但是劉昌明認為還應該關注雨水,中國全年降水量,是全國用水量的十幾倍。如果能把雨水充分轉化為地下水,那水資源基礎就大大增加了。
同時他認為,中國節水潛力仍然巨大,農業可以省出 30%,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可以從 60% 提高到 80%,通過杜絕浪費、管道滲漏和回收處理廢污水,城市生活用水還可以節水 1/2 到 1/3。
Parton 承認中國政府近年來為了緩解水資源短缺所做的各種制度建設的正面意義。無論是“三條紅線”、“水十條”、 《環境保護法》、河長制和湖長制,還是“海綿城市”和廢水回收利用。只不過這些也都還不夠。
他認為,中國必須為了應對他所說的“水危機”而開展經濟轉型。用 2 月他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的話說,要轉型為一種“駱駝經濟”。
這意味著:工業應該盡快用高新技術和服務行業來替代鋼鐵、鋁制造、服裝、造紙等高耗能/水的行業。電力供應首先應該降低需求,并充分利用非化石能源。在農業上,則必須放棄對政治上高度敏感的糧食自給的強調,轉而從國外進口更多農產品——因為進口農產品,特別是高耗水量的農產品就相當于進口大量的水。此外,灌溉應該變得更節水,因為低效的灌溉浪費了中國 30% 的水資源。他甚至還建議進行土地改革來促進農地兼并——一個同樣政治上敏感的話題,即便并未說明為何節水需要大型農場。
Parton 認為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水價實在是太便宜了。這是提高用水效率的主要障礙,2011 年時中國水價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時單位產值的用水量數倍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這個問題牽涉到失業和通脹,涉及社會穩定,所以政府長期沒有作出調整。
說了很多年的“中國水危機”
關于中國“水危機”的討論,在此前曾多次出現。一些標志性文本的問世,無疑貢獻于相關論述的形成。
早在 1999 年,資深環保工作者馬軍就出版了《中國水危機》一書,指出中國一味試圖以水利工程治水,卻忽視流域生態保護,50 年來 8 萬座大壩建成,同時大片的森林卻消失了,這造成中國水旱災頻仍。如果西北、華北不改變當前大量消耗水資源的生產生活方式,即便是當時熱議的從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長江向黃河調水也無濟于事。馬軍當時就提出,變工程治水為生態治水,是解決中國水資源問題的唯一出路。2004 年,這本書被譯為英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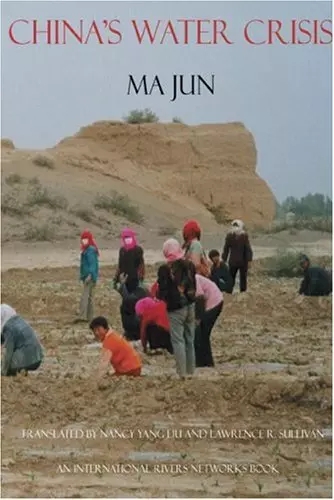
馬軍《中國水危機》的英文版封面
2005 年,當時的水利部長汪恕誠就曾告訴記者,“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要珍惜每一滴水,否則就是滅亡。”這句話后來被外國媒體在談及“中國水危機”時廣泛引用,此番Charlie Parton 的報告中也以這句話開篇。
2009 年初,世界銀行在北京發布了報告《解決中國的水稀缺:關于水資源管理若干問題的建議》,指出中國“年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均擁有量最低的國家之一”,而北方地區的水資源短缺人均擁有量更是只有 757 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11,低于“短缺”閾值(1000 立方米)。報告援引世行另一份報告的數據:中國“水危機導致的經濟損失已約占中國 GDP 的 2.3%。”
2010 年,世界銀行旗下的“2030 水資源小組”(2030 Water Resources Group)的一份報告預測:中國在 2030 年將面臨 1990 億立方米的用水短缺。短缺部分,占那一年中國全部用水需求量 8180 億立方米的 24.3%。這在當時《中國日報》的報道中,也被稱作“水危機”。
2012 年,美國政府發布的一份關于安全風險報告曾預測,中國到 2030 年將因為缺水而出現大規模的糧食短缺,因而構成一項地區安全風險。
還有為數眾多的英文媒體報道、評論,都曾使用“中國水危機”的表述。
但是,“危機”并不是一個客觀的科學概念,它取決于人們的主觀認知和態度,和對困境的容忍和適應能力。
劉昌明院士在 2009 年接受前述《科學時報》 的采訪時,將中國廣泛的水污染,以及地下水超采和與之伴隨的地面沉降和濕地消失,都看作復數的“水危機”。談論危機,并不需要等到水不夠用了。
在中外對話的網站上,在 Parton 和 Rogers 團隊的交鋒之后,6 月 6 日,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研究員王姣也參與了討論。她的文章《水壓力:看待中國水危機的另一視角》并未沒有進入有關 “有沒有水危機?”的辯論,而從數據上看待中國地區間的水壓力變化。
不同于法爾肯馬克指數用一個“人均”數據籠統地描述一個國家或省份的水資源量,王姣的研究采用更豐富翔實的數據,呈現出水壓力在空間上更復雜、真實的分布狀況。
她對比了 2001、2010 和 2015 年三年的中國不同流域水壓力的數據,發現 2010~2015 年間,中國高水壓力地區面積還是在增加,但是增加速度要低于 2001~2010 年。同時,這五年間,水壓力加劇的地區的總面積僅為前 10 年的 35%。
如果這種“加劇速度減緩”的回答還是給人一種喜憂參半的感覺,那么下面這個更像個好消息:2010~2015 年間,水壓力得到緩和地區的總面積是 2001~2010 年總面積的 10 倍。
但是地區間的反差還是十分強烈。這后 5 年與它前 10 年相比,黃河上游和長江上游地區的水資源壓力有所減輕,而黃河下游地區的水資源壓力還是加劇了。此外,華北平原在這 15 年中始終處于極高水壓力下,雖然農業灌溉用水不斷下降,但是工業用水持續上升。
但是從全國而言,王姣仍然認為這些年來的變化是積極的,表明國務院 2012 年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三條紅線”以來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初見成效。這所謂的“三條紅線”,分別對 2030 年時全國的用水總量、用水效率和污染物控制劃出了底線。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另一個研究團隊還發布過一份 2040 年全球水壓力最大國家的排名,其中前 33 名主要是中東、中亞、北非國家,沒有中國。但是報告同時指出,屆時中國和美國、印度一起,都將面臨持久的高水壓力。
